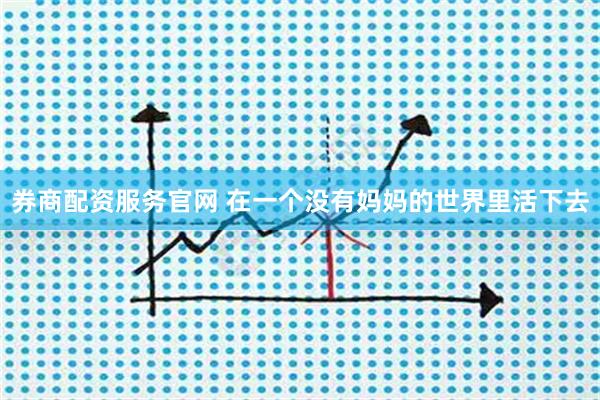
作者:俞瑾券商配资服务官网
我们无论失去什么,都要活下去。
建初把帐篷搭在了坑里,早上起来,腰疼得厉害。下山就上了高速,从隆尧去涉县,查到那边有个能泡温泉的地方。
沿途没有加油站,只能又从高速下来走国道。到了温泉门口,保安拦着不让摩托车进,说“之前来的摩托车都没开进去”。跟前台反复沟通了很久,才被允许把车停到楼下。
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:在这个世界上,有力气去坚持、去沟通、去对抗的人,确实能在同一套规则里获得更多空间。可也有很多人,从出生起就被教育要顺从,他们甚至不理解,为什么有人会试图多说一句。
展开剩余78%终于泡进水里。
风声停了。
安静比寒冷更容易让我感到战栗,后背的疼痛逐渐随着热水一点点的消融,身体松下来,思念和舒适便随之漫上来。鼻尖开始冒汗,我分不清是昨晚在山顶受了寒,还是最近真的太虚了。建初转头看我时,我已经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你不可能不去想,脑子不听指挥,你再怎么希望自己快乐,意识一旦变得模糊——刚醒来,或将睡去——浮上来的永远都是妈妈的样子和声音。
从非洲回来那次,我妈嫌我的睡袋太臭了,把我斥巨资买的俩个鹅绒睡袋直接扔洗衣机里洗了。昨晚露营,睡袋晾了半天,怎么都蓬不起来,保温效果明显差了很多。
突然好想给老妈打电话抱怨两句,抱怨她的洁癖,她的勤劳,她的多管闲事……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……想起妈妈的微信头像,是她养的一盆花,那朵花,再也亮不起来新消息才会有的红点了。
好难相信啊,我的妈妈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,她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
是我陪着她离开的,眼看着她的气息越来越弱,直到早晨的太阳洒在她的身上,指尖的仪器再也测不到她的脉搏。那天晚上医生来过,她问我:你喊妈妈,妈妈还醒吗?我说我没喊过,让她好好睡觉吧。
血压往下掉的时候,另一个男医生推来机器,说可以注射升压药,试着抢救。我摇头,说不用了,让妈妈好好睡觉吧,她本来血压就低,人生里只做过一次胆囊手术,打完麻药,血压就直线下降,那次把麻醉师都吓坏了。医生想说什么,但我坚决的摇摇头,他懂了,带着护士离开了。
我知道妈妈平时最讨厌人群,不喜欢被人盯着,回家都不走大路,宁可绕远,避免和邻居寒暄。现在,我护着她安安静静的睡着了,身上除了针眼,没有任何刀口,到离开也没有插过任何管子。在她的最后几天,即便在医院,围在她身边的,只有她爱的人,和爱她的人。
可我明明陪她到最后,亲眼看着她的身体落入黄土,怎么就如此不相信,她真的不在了呢?她消失了,她死了,这个世界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了。
对于旁人只是自然规律,生老病死,世界没有发生丁点儿改变。可对于我,太阳被拿走了,世间不再有阳光,不再有温暖,属于我的世界已全然变了。变得好陌生,像一场随时可能醒来的幻梦。
妈妈之前没有生过病啊,半年前她还是那么健康的人,我开着一辆画满涂鸦的大篷车,带回家七八个天南海北的小伙伴,她还给我们做了炸酱面呢。
可现在她却没了。
我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,被老天一秒一秒的收走了,她消失了,变成了一座坟头。
那回的炸酱面,居然是我这辈子吃到的、妈妈做的最后一碗炸酱面。老天爷,能不能让我回去再多吃一碗?
一想到这些,我心里就发慌、发毛,只能强行把注意力拽回热水里。
如果妈妈不是被突如其来的绝症带走,如果她是像姥姥、姥爷、爷爷、奶奶那样,走路慢慢变得颤颤巍巍,最后走到生命尽头的。也许我就不会这么难以接受。
可她不是。
她是突然离开的。
突然就不能再发出声音了。
她最后说的,还是一句:我嗓子怎么了。
她用尽全身力气,在我手心里写了一个金字旁,又写了一个“好”,然后,紧紧地把我往怀里摁。
我们彼此那么不舍得,这一世的母女缘却刹那间断了。我去找医生的时候没掉一滴眼泪,我们坐在两把没有隔着任何东西的椅子上,谈论吗啡会带来的呼吸抑制,谈论安乐和安宁。如果家属不够理性,医生也不敢轻易开足量的吗啡和镇定让病人睡着。那一整夜,我都在告诉妈妈好好睡觉,不用再醒来受苦了。
缘已尽情未了。
换谁受得了,谁能轻易释怀得了。
确诊到治疗的一个半月,我拼了命的想让妈妈多陪我几年,哪怕几个月,要知道未分化甲癌的中位生存期只有六个月;最后的几天,我又拼了命的想法儿让她早点睡着,脱离已经无法逆转的痛苦。她赠予我生命,我却只能绝望的决定、接受、看着她死亡。
那两个月的理性,是牙把心都咬烂了,等到都过去了才回过神。
我的保护神离开我了。不管世界上有没有灵魂,她还能不能看见我,我都再也看不见她了,再也听不到她说话了。
可无论失去什么,都要活下去。
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,手心还在发热。
好像刚刚,还被人紧紧抱过。
如有侵权券商配资服务官网,联系删除。
发布于:河北省五八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